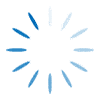见两张淡金色的面孔笑着从余晖里走出来,五条悟有些神思恍惚,不知道怎么错以为看见了从前五条律子牵着他走过的无数个黄昏。他迎过去,越走越近,她的面孔越来越清晰,脸上的笑意却淡了许多,就像回忆一样,过去的,不论好与坏,再提起来总是有一种抹不开的哀愁。
伏黑惠仰着头看五条悟走过来,举着手里的花打了个招呼。
五条律子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避开了五条悟的目光,低下头将手抻长,半拉着伏黑惠往前走,嘱咐他,“进去让筱原阿姨给你把这些花摆到房间里,再洗脸洗手,准备吃饭。”等他点头抱着花颠颠地进了家门,她这才抬头看向五条悟。
“怎么今天回来得这么早?”
他伸手去握她垂在身边的手,“想和姐姐你们一起吃饭。”
她在他手心里不自在地动了两下,等他握紧,才安分下来跟着他往回走,“有些事想和你说。”
他往她那边靠过去,手臂紧挨着她的,“什么事?”
“惠已经到了该送去读书的年纪。”伏黑惠刚到家时,她不放心让他在还没有适应新环境的情况下又被迫适应另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一直留他在家里待着,时间过去近半年,才提起这件事。
五条律子从没上过学,从小到大都是私人教师独立教学,那其实也说不上是教学,她学的从来都不是什么知识,只是一系列如何让她的身价更加高昂的培训。这导致她对学校没有任何概念,只能从旁人那得到一点片面的解释,就像是从门缝里去偷偷看一个从没有进入过的世界。
这些她没经历过的,她不想让伏黑惠也错过。
“幼儿园吗?”
“嗯。”
“等周末我陪姐姐去附近的学校看看。”
“远近倒是不重要,可以叫司机接送,”她一说到伏黑惠的事情,就忘记了在他身边的紧张,神情跟着放松,“主要是环境还有老师,惠这样的性格,需要一个宽松又自在的环境,这得多考察一段时间。”
“嗯。”五条悟低下头,眼望着和自己双手紧握的她,只见嘴唇在翕动。
又想起了小时候,只不过过去的时间太久,她对自己说过什么,早就不记得。近几年的倒是记得,她就坐在自己旁边,想要听他说出门之后见过的事情。她不嫌烦,总是嫌他说得不够仔细,恨不得借他那双眼睛把他见过的都看个遍。然而那会儿他心思早就跑到了不知道哪个角落,哪里还记得外面,眼睛也只光顾着往她脸上看,看她眉眼间那一星半点的颤动,像夜里忽闪的星星。
时隔多年,这些模糊的声音又一次在他空荡荡的胸腔里回响了起来,字字句句听不明白,他有些可惜。
“再过几年,他还需要书房,需要自己一个人的环境,还有电脑——”
“姐姐。”他打断她。
“嗯?”
“读书这事反正要花一点时间,趁这个机会,我们出去旅游吧。”
“旅游?去哪里?”
“去国外怎么样?”
“国外?”她此时的表情看起来有些愣乎乎的。
“对啊,去从来没去过的地方玩一玩。”
五条律子眼睛微微睁大,“为什么突然想到去国外?”
“想让姐姐更高兴嘛,姐姐不喜欢出去看看吗?”他凑过去在她发间亲了一口,“而且姐姐今天看起来不怎么开心。”
她不由自主地放慢了呼吸,小声说:“我现在很好。”
“能更好的。”
她抬起眼睛看着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这时正巧余光见伏黑惠朝她跑过来,顺势从他手里把手抽了出来,装作若无其事地去迎接伏黑惠。
话被她搪塞了过去,饭后也再没提起。
伏黑惠惦记着五条律子答应的事情,自己吃完饭就眼巴巴地望着,只是因为五条悟在,他没说话,一直坐着把下巴磕在桌子上等她。她摸了摸他的脑袋,劝他回房间等,自己先去洗个澡。听见他们说话的五条悟这时突发奇想,要陪伏黑惠打发这段时间,五条律子虽然觉得听起来有些怪,但说到底还是希望他们不像之前一样两只眼睛一对上就互相看不惯。于是再三强调要五条悟别欺负伏黑惠后,就放开手自己进了浴室。
结果等她从浴室里出来,在房间里等着她的是脸上画了两个完整乌龟的伏黑惠和脸上也一样画得花里胡哨的五条悟。
他们在玩佩尔曼纸牌游戏,谁先翻出两张一样的纸牌,谁就可以在对方脸上画画。五条悟这个厚颜无耻的高中生仗着自己年纪大记性好,碾压式欺负一个幼儿园小孩,非但没觉得胜之不武,在五条律子看过来时,还格外自豪地说:“我就输了两次。”
五条律子:……
见伏黑惠玩得起劲,她也没开口说他们,笑着哄伏黑惠去找阿姨帮忙擦掉脸上的颜料,回头才念叨五条悟,“和他比记忆力,也亏你做得出来。”
“小孩子觉得好玩嘛。”
“我看你比他还觉得好玩。”
“这又不冲突。”
她见他带着脸上那些五颜六色的水彩颜色往自己这走,催他去洗脸,“不要把这些颜色到处蹭,也不知道洗不洗得掉。”说完就打算出去看伏黑惠。
只是还没动就被他拽住,手臂一张就要抱她,“姐姐帮我擦。”
“你又不是小孩子,”她一脸嫌弃地推开他,“别蹭到我身上。”
她越是嫌弃,他就越是不讲理,“姐姐帮我擦干净,不就不会弄到身上。”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不能。”
最后还是争不过五条悟,五条律子出去找人拿了点湿纸巾过来帮他擦脸上的颜料。就地跪坐在伏黑惠房间里那张矮桌子旁边,五条悟微微低头,注视着她的脸,刚跑过热水浴的皮肤上烘着一股湿漉漉的暖气,细细的汗毛上隐约浮动着细细的亮光,让她这时候凑近的脸难得看起来有几分亲近的人气。
“姐姐,我们第一次从五条家出去的时候,”他扶着桌子边的手动了一下,“你说你很开心,”那时候她在街道路灯下的脸仿佛在发光,仰着头看他,满满一轮月,“我以为你喜欢出门玩。”
她的动作停顿了一下,“我是喜欢。”
“只是不喜欢出国吗?”
五条律子不知道怎么就想起了很久之前从别人那听来的故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景,“……我又没出过国,怎么都说不上不喜欢。”
“那去试一试怎么样?”他歪着脑袋打量她,“正好惠那小子还没上学,有的是时间。也可以当作庆祝他入学,我们一起出去玩。”
“出去玩?”话让洗过脸刚进门的伏黑惠听见了,他吧嗒吧嗒跑到他们身边,“我们又可以出去玩了吗,妈妈?”
“对啊,”五条悟见他这么起劲,接着说,“出国玩怎么样,惠还没去过吧。”
“出国?”
“就是日本以外的地方。”
“那是哪里?”他一脸好奇。
五条悟有意诱惑他,“去非洲那边怎么样?可以看活的狮子,狼,大象。”
“上次去动物园看过了。”
“去非洲可以摸得到哦。”
五条律子这会儿没搭腔,帮五条悟擦掉最后一点颜色后,就坐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他们。伏黑惠听完发出一声兴奋的惊呼,趴在她膝头兴致勃勃地追问,“妈妈,我们之后要去摸狮子吗?”
五条悟也跟在一边看她。
她问伏黑惠,“你想去吗?”
“想去。”
她这才抬起脸,回望五条悟,笑容就像脸上那阵热气,朦朦胧胧的,涎着双眼里薄薄一层愁雾,“那就去吧。”
后来五条律子忙了两个月,几乎都要忘了这回事。总是要出门,频率比以往都高,偶尔带着伏黑惠,偶尔不带,看了许多学校,怎么都挑不好。要么觉得环境太老旧,看上去呆着人不舒坦,要么觉得环境太闹,看上去不怎么安全。东京当地的学校不少,但挑挑拣拣,看了就总能给她挑出毛病来,久了自然就喜欢不起来。
她以前根本没觉得自己是个挑剔的人,结果发觉这些天下来一无所获,倒是把她自己先吓了一跳。愣坐着许久,也没想明白到底哪里不顺眼,只走进去,就跟手指头上的毛刺一样刺剌剌的痒,深了就开始疼。
想得太入神,五条悟什么时候坐到身边都没察觉。他没碰她,她也就没被惊动,两个人肩膀挨着肩膀这么做了好一会儿,像是顺着时间漂流,躺在没有尽头的沙滩上不说话。
慢慢地,他的脑袋靠了过来,压在她肩膀上。嘎吱一声,她心里头的声音响亮地回荡在耳道内,是什么要被压垮的声音,摇摇晃晃的,浓重高耸的黑影在四分五裂的地基上即将塌毁。她惶惶然地抬头,去看他,“悟?”银白色的短发压在她肩窝和颈侧,戳着软肉,一阵耐不住的痒。
他没吭声,只是把手伸了过来,握住她放在膝上的手,穿过她的指缝紧扣着。依旧这么一动不动地坐着,盯着两只缠绕在一块的手看了一会儿,那阵痒就成了扎在皮肉里的疼。
五条律子这才知道自己在挑什么,看不惯什么——是眼看着摇摇欲坠的楼房在早已经塌陷的地基上颤抖,住在这里头的人看什么都跟自己一样在晃悠,眼里见不到稳当的东西。
就在她这么苦想着,听见身边一阵闷响,“杰叛变了。”滚雷似的炸开来。
她没接话,就这么听着,听完那些血淋淋的惨案,连手指头都是冰的。
他说:“杰想要创造只有咒术师存在的世界。”
“只有咒术师的世界?”
“没有这些人,诅咒就会消失。”
她闷着声,忽然问:“那活着的人又该怎么办?”
“也许……一切照旧吧。”
“即使诅咒消失了,苦难也不会消失,怎么能照旧,”她偏着头看向房间外面白苍苍的天,缓声说,“人心,哪有那么容易愈合,悟。”
“我该怎么做,姐姐?”
“我不知道,正视普通人的苦难本来就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窗外空旷高远的天空下,她的叹息声如此微弱,“更何况……是拥有六眼的你。”
话刚说完,他直起身,伸手过来将她的脸的带过去。手放开她的,又压到她的后腰上,将她拉进怀里,极轻地吻了她,只是两片嘴唇贴着。
她的眼睛阖了起来,手扶着他的手臂安静地呆在他怀里,鼻尖闻到了他身上的气味,带着温度的,悄无声息地就蔓延到了她身上,热腾腾地蒸进骨头里。她很快放松了紧绷的肩膀,任由他拥抱着自己,身体内的不和谐的声音,都在他的唇齿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吻过,他将脑袋埋进她肩膀,热气全喷洒在了她衣服底下,再被他双臂紧紧束住,她成了他呼吸里的囚徒。
五条悟又请了假,说是要和五条律子去物色新的幼儿园,一连好几天都在家里呆着,说是陪,倒更像是守。她心里清楚他有什么事装着没说,懒得问,心思全被她放在了别的事情上,这回倒是顺利,她突然就不挑了,看什么都还算满意,这样仔细比对过后,就看上了综合水平最优的一家幼儿园。
深入了解过几天,园长就热情邀请她过些天去参观幼儿园,了解他们入学后的日常生活。五条悟的假期已经结束,她是一个人过去,正巧碰上了幼儿园小班在园游会彩排话剧,在院子里坐了小半日,看他们演排竹取物语。
什么都很巧,她想。
五条律子坐在最后排和老师们一起看这一溜圆滚滚的脑袋围坐在一起,正中央的小演员一本正经地扮演各自的角色。饰演辉夜姬的女孩坐在最高的位置上,因为是彩排,只是简单地披了件彩色的纱布在身上,不过胜在女孩天生可爱,动起来有种俏生生的鲜灵,一切都看起来融洽得刚刚好。
辉夜姬独自坐在高台上,“求婚”的角色一个个走上来,一个个空手而归。因为演员年纪小,耐性差,这几步路的表演总是有人忘词的或者临场发挥,台下面因此笑个不停。老师们也觉得这样效果不错,倒也没喊停,或者纠正,就让他们这样继续演下去。
唯一没错词也没忘词的是坐在中央的辉夜姬,求婚者离去,天皇驾临,逼迫她入宫不得,又纠缠多时,即将归月的她对着伐竹翁夫妇二人那番告白每一句都那么清晰。五条律子下意识就想起了原书里的那番话,“可是这一切都由不得我做主,我也无可奈何——”
此时为防辉夜姬离开,天皇派重兵,严防死守。台下有个小小的声音回过头来说:“老师,有只很大的鸟。”原以为他指的是即将上场扮演月宫仙鹤的演员,可仔细一看,他手指的方向分明是头顶。
心里一顿,五条律子跟着抬头,只听见几声不知从哪里来的长鸣,身后筱原的声音骤然被吞没,巨鸟展翅,遮天蔽日地盖过了她的双眼。
“老师,大姐姐到月亮上去了!”骚动的人群里有小孩在大喊。
干燥的风拍打在脸上,她睁开眼睛,面对着夏油杰。
他说:“特地牵着云来找你,带你去看月亮,去不去?”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