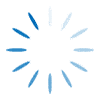好!
江廉恶狠狠瞪着宁州书馆的牌匾,“就算是金光侯的亲弟弟,升平郡主的小叔子,本官身为朝廷命官,也要为百姓主持公道!”
啪啪啪。
有人鼓着掌出来了。
就一个。
还是萧讷,身后跟着明显气坏了的萧长魁,沉着脸的尉迟均。
“大人爱民如子,老朽佩服之极。不过要打官司,须得状纸。如今有人告状,可有状纸?”
江廉一噎。
他太久没干正经事,完全忘了。
却不想遇到萧讷这样的老状师,一句话就把他怼了回去。
转头问,“你们的状纸呢?”
彪形大汉们面面相觑,哪有什么状纸?
他们就是收钱来闹事的。
白纸黑字的东西,谁敢乱写?
萧讷淡然,“请问这位苦主,你说是我这外孙抓错了药,害死了你爹,证据在哪呢?”
瘦小男子目光闪烁,都不太敢接话。还是被那些大汉狠瞪了几眼,才硬着头皮道。
“那,那我爹都死了,还不是证据?还有他吃剩一副药,你们瞧,这里头就有那个,香加皮的……”
萧讷呵地一声冷笑,“你爹死了,就算是死于抓错了药,但你也不能证明,是我外孙抓的药吧?”
这……
田巩等人对视,皆明白了大半。
瘦小男子越发支支吾吾,旁边大汉勉力帮腔,“那日明明就是他,他把人带去的。”
“但我也不可能抓错药!”
尉迟均黑着脸上前,紧紧攥着拳头,却克制着自己,没有发火。
“因为那天特意有交待过,是五加皮,不是香加皮,我记得清清楚楚。去药铺的时候,还拿了方子给伙计看过,对了好几遍。”
那大汉强词夺理道,“你这会子自然推得一干二净,横竖是你家的地盘,肯定都帮着你。”
“你!”
萧长魁气得浑身直抖,话都说不利落了。
谁想尉迟均沉住了气,“哦,你们既知道这是我家地盘,还敢来闹事,那是仗着谁撑腰啊?”
这话问得极好。
连虞希都忍不住赞赏的点了点头。
当下有百姓高声答,“听他们口音,是济州人。”
呵!
呵呵,原来是济州来的。
那些士兵一听,拳头捏得嘎巴嘎巴作响,主动问,“各位大人,要不要先把他们揍一顿,揍老实些再问?”
“你们敢!”
江廉一副义正辞严,大义凛然的模样,揪着尉迟均方才的话,挑他的毛病。
“什么你家的地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算金光侯于国有功,但家里人竟敢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可见平日里如何嚣张跋扈!”
哪有这般倒打一耙的?
连田巩这样老好人都气着了,“江大人,这话可不是尉迟公子先说的,是他们先说的。你这么断章取义,偏袒他们,到底是何用意?”
“我怎么偏袒他们了?难道非跟你们一样,都巴结着尉迟家,才算是公道正义?”
江廉到底是当过御史的人,胡搅蛮缠起来,可是十分的在行,还假惺惺道,“田大人,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忧。就算你们身上穿的斗篷,还有些大伙儿看不见的好处,皆是金光侯和升平郡主给的,但你到底还是读了圣贤书的朝廷命官吧?能被一点子小恩小惠收买,不公不正?亏我从前还以为你是个老实人,原来骨子里也是这般的市侩!”
田巩本是个老实人,不擅于人争吵。此刻气得脸都白了,浑身颤抖,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虞希笑了,“那依着江大人的意思,今儿您是非当这个江青天,要做这个主了?”
“正是!”江廉高高昂着头,“有本官在,这寿城,这宁州,就轮不到尉迟家一手遮天!”
好好好。
你自己作死,就索性成全你!
虞希冷着眼才想挖坑,不防一个声音响起。
“那江大人不如赶紧回衙门,去参本郡主一本吧。”
是许惜颜,坐着马车来了。
在打发琥珀过来送了号牌之后,她听说今儿百姓特别多,到底不安心。又拉了几车柴炭,找邻近的几家大户人家,收拾了些不用的被褥,亲自送来看看,不想就遇到江廉闹事了。
此时她也不多问,只在马车里淡淡吩咐。
“把那些闹事的拖下去,俱都打折双腿,扔去济州边界。”
什么?
众人皆惊。
江廉更是道,“你,你竟如此心狠手辣,就不怕有伤天和?”
可郡主府的侍卫统领,段猛已经冷哼一声,招手带人上前了。
但这种粗活,哪里还用公主府的人动手?
在场的副将,赶紧给手下递个眼色。
兵哥们上前一围,直接提起拳头就开揍。
他们受了郡主大恩,如今有机会,自然要回报一番。
再看这些来闹事的,一个个恶形恶相,也不知是哪家养的打手。若是高家养的更好,先狠揍一回,出出多年来的这口恶气!
好些围观的百姓,还帮着出黑拳,递棍子。
郡主说了,要打断他们的腿,靠手多累得慌,还是用棍子快。
可边军兵哥的凶悍,还是远超百姓想象。
以为用拳头就砸不断他们的腿?
那就给你们现场露一手。
咔嚓!
有个看着身形中等,不太魁梧的兵哥,却是一拳带着风声下去,就把一个大汉的小腿骨生生打折了。
痛得他惨叫一声,晕死过去。
可是还没完呢。
段猛森然冷笑,“郡主都说了,是两条腿!”
然后他猛地一踹,将那人另一条腿骨也给踹折了。
原本痛晕过去的人,又痛醒过来。
鬼哭狼嚎的惨叫声,简直突破天际。
余下之人,跪了一地。
“郡主饶命,郡主饶命!”
“郡主,只要你饶过我们,我们就告诉你幕后主使!”
可升平郡主,一点也不稀罕知道这个幕后主使。
接下来,无一幸免,所有来闹事的人,全都给打断了双腿。
那瘦小男子,早吓得面无血色,瘫软在地,尿湿了裤子,骚气冲天。
江廉,江廉最开始还叫嚷几句来着,后面也给吓得变了脸色。
缩到人群后头瑟瑟发抖,生怕许惜颜注意到他。
这一刻,他才突然意识到,何谓贵族,何谓皇权!
场中数千百姓,静得连根针落下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