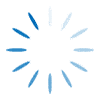见许樵不肯多说,许云樱心中不悦。一双妙目盯着那位越皇孙的挺拔背影,忍不住怦然心动。
前头说的那些贵人她不熟,但这位越皇孙却是在京城颇有名气。
睿帝子孙繁茂,宫中长大成人,有名有姓的皇子就有二十好几,皇孙更是不计其数。
但其中最出名的,便是这位端王世子,被谑称“大齐第一黑”的萧越了。
他名字里的越字,来自吴越的越。
只因他的亲爹,已故二皇子,当年迎娶的是吴越首富石家的独生女。
那年睿帝下江南,伴驾随行的二皇子,意外与号称江南第一美人的石小姐相遇相知。
睿帝一高兴,便成全了二人好事。
只可惜这位石美人,做了二皇子妃不到一年,便在生产时因血崩而亡。
素来体弱的二皇子,伤心新妇过世,很快跟着去了。
而石家外祖闻讯,悲伤不已,不久也染病过世。临终前将家中数代积攒,据说富可敌国的财富,托付于皇室掌管。
皇上心生怜惜,便将过世的二皇子,也是所有皇子间,唯一一个封了端王,也给了萧越亲王世子的待遇,算是皇孙中的第一人。
后来机缘巧合,也不知是谁,偶然把萧越带到了成安公主面前。
那时成安公主还未嫁人,就象大皇子会怜惜年幼丧母的成安公主一般,妙龄少女就算再娇纵任性,但对于一个当时走路还摇摇摆摆的软萌小侄儿,自然多了几分爱心。
姑侄俩理所当然的好了起来。
而跟着成安公主厮混长大的萧越,也跟这位皇姑一般不学无术。
既不爱读书,也不爱练武,更没有半点外祖家,世代流传的生意天份。据说见了数字就头疼,生平最爱在泥地里捣鼓东西。
还不是捣鼓那些奇花异草,高雅之物,偏只爱捣鼓瓜果蔬菜,果树禾苗。
据他所说,能入口的东西才值得种,那些中看不中吃的花花草草,哪怕是梅兰竹菊,有甚意思?
如此一来,许多自诩高雅的读书人,看不上这等人。
又因闹过从马背上跌下来的笑话,长大了还只拉得动小孩用的软弓,武将也瞧不起他。
于是这位越皇孙,成了宫中的异类,走哪儿都不受待见。
但在护短的成安公主眼里,这都不叫事儿。
天生就是最尊贵的皇族,爱种地怎么啦?高兴种就种呗。
所以受宠的她,还在睿帝跟前,为这位皇侄在掌管农事的户部,讨了个七品的小主事。
不给实权无所谓,重点是给他划一块地,弄些东西给他种就行。
睿帝被她歪缠得无法,只得允了。
在京效皇庄里拔了一块山林,随他折腾去了。
从此,越皇孙就成了京城人尽皆知的“种田皇子”。
因为成天下地,风吹日晒,自然肌肤黑些。有一回被某皇叔瞧见,打趣他是“大齐第一黑”,他也欣然接受,算是坐实了这个绰号。
许云樱从前听说,只当是个笑话。
好好的皇子不当,当个农夫有甚意思?
但今日在亲眼见到真人之后,她不这么想了。
就算爱种田,肌肤微黑,但萧越却也是一等一的好相貌。
又是十八九岁的好年纪,高大挺拔,如此就很能吸引年轻女子的目光了。
许云樱今日见了成安公主的派头富贵,不由得对嫁进皇室,怦然心动。
她身份低微,想嫁尊贵皇孙估计有点难,但若是选这位种田皇子,应该勉强可以的吧?
反正这位越皇孙有生母遗留的大笔嫁妆,怎么说将来日子都不会差。
那到时,她就是皇孙妃,就算许惜颜是郡主,也得给她屈膝行礼,哪里还有架子可摆?
许云樱越想越觉得可行,便想着要怎么抓住机会,在萧越跟前表现一番,引起他的注意了。
但方才许云梨的教训,让她知道自己不可造次,尤其上头还有成安公主这头母老虎,那该怎么做呢?
正好那边三人谈话完毕,萧越答应回头派个人去看看许云津的田地,送他几棵果苗。
“……要是地方合适,不如从我那儿扦插些葡萄藤过去。那个好养,长得也快,入夏就能收果,到时便是现成的银钱了。要是不急着用钱,不如给我酿酒。我去岁从胡人那里买了个酿酒方子,几个下人做得还行。到时酿好了葡萄酒,依旧还你,搁到年节去卖,却比单卖葡萄利息高多了。”
许长津感激不尽,再次拜谢,和许观海一起,送他出去。
许云樱心里一急,忽地心生一计。
抓了只青翠粉红的小鲜桃,遮遮掩掩就扔了出去。
萧越正想扭头跟许惜颜打声招呼,冷不妨一只桃子骨碌碌滚到他脚下,眼看他一脚就踩了上去。
“小心!”
才瞧见的许云槿惊呼出声,但还是来不及。
却有一道少年身影,忽地从末席起身。
到底人形醒目,萧越吃了一惊,赶紧住脚,险险站定。
许观海一下就怒了,“是你丢的桃?”
“不是我!”看着地上桃子的许云柳,赶紧摆手,“是二姐姐在冲我招手,我才站起来的。”
谁丢的,他没看见。
许云槿忙起身道,“回父亲的话,不是五弟,是樱二姐姐扔的。”
许云樱满脸惶恐,却身姿优美的款款站起,娇声认错,“是,是我。三叔,您别生气,我,我也不是故意的。就,就一时手滑了。世子殿下,对,对不起……”
少女咬着樱唇站在那里,已经有晶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了。
如梨花带雨,楚楚动人。
可萧越只扫了她一眼,便捡起那只桃子,走到许惜颜面前,笑出一口白牙,眼神温暖又透着亲昵。
“阿颜是怕我摔着,才把你弟弟叫起来的吧?多谢你啦。只这桃子摔过,就不好吃了,但还能拿回去酿果酒。待我做好,再给你送来呀。”
许惜颜低头行礼,神色淡然,“举手之劳,皇孙客气。”
“你呀——”
萧越似有未尽之言,到底没说出口。只轻摸了摸许惜颜的头,然后将那只鲜桃好好收在袖里,心满意足的走了。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