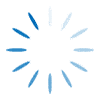车一停下,那人就拽开后车门坐到了另一边。
“您去什么地方?”司机热络的问。
那人伸手把帽檐压低,“鑫源小区。”
司机倒吸口凉气,脸色刷的白了,冷汗顺着鬓角流了下来。
“不走么?”那人问。
司机上半身前倾,一只手搭在车门上,双腿肌肉绷紧,从后视镜看了我俩一眼,嘴里说着“走”,转头就拉开车门跳出去,玩命的跑,边跑边喊:“鬼啊!”
我这才反应过来,司机这是觉得自己遇到阴人搭车,吓得出租车都不敢要了。
不过,没准还真是阴人搭车。
我扭头看向坐在我旁边的人,他低着头,车门已经被打开一条缝,看起来也是想要下车,之所以没下成是因为血线已经缠住了他的胳膊。
“去鑫源小区干啥?”我压下心里的紧张,冷着脸问。
那人抓着手里的黑包,不抬头也不说话。
血线猛地收紧,那人闷哼一声,哆嗦着说:“去六号楼送东西。”
我看了眼他的黑包:“送啥?”
他突然把黑包扔过来,同时一脚踹开车门,也不管胳膊上的血线,直接跳了出去。
我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右胳膊被扯下来,转瞬化成一团黑气。
“啊!”他惨叫着跌出车外,连滚带爬的逃进路边的胡同。
我要去追却被饶夜炀拦住,他从石像里出来,说:“不过是个要去参加鬼祭的小鬼,跑就跑了。”
他这么说,我就没再坚持,好奇的打开黑包,发现里面竟是骨灰盒。
我浑身发毛,忙着放到一边,从车里下去。
“他去鑫源小区,拿着个骨灰盒干啥?”我不解道。
饶夜炀解释说:“参加鬼祭需要用到骨灰,他们得把自己的骨灰撒进那圈蜡烛里,这代表他们诚心归附,毕竟骨灰对付鬼魂来说极其重要,想要控制他们就需要夺得他们的骨灰。“
我明白了。
心思一转,我笑着问他:“仙家,那你的骨灰是在是石像里吗?”
“不是。”他道。
“那你咋离不开石像?”我纳闷的问。
他睨我一眼,“再不去车库,天都要亮了。”
我看了眼时间,发现已经快要十一点了,也顾不上纠结他的骨灰,忙着往鑫源小区走。
今天也是邪门了,街上的出租车特别少,网上也没人接单,最后我是自己跑着过去的。
看来,我得买辆自行车,不然出门太不方便。
我赶到车库时,已经是十一点半。
饶夜炀说:“十二点前必须出来。”
“知道了。”我应了声,翻过铁丝网,从车辆入口的斜坡往车库里走。
车库里乌漆嘛黑的,靠着手电光,我只能看个大概。
入口通道处又脏又乱,堆着许多废旧钢筋石料,一股子尘土味,不过墙壁和水泥地却很干燥,没有渗水的痕迹。
江阴市虽然在北方,可雨水并不少,车库里这么干燥,难道是当时已经建好了排水管道?
车库是螺旋入口,转了一圈才来到停车场,这地方很大,有梁柱和墙壁隔着,我只能看见靠近入口那一块区域,要想窥探全貌,还需要往里走。
我举着手电抬头看,顶子上的水泥已经抹好,还铺设着电线。
孙大勇得到的消息是错的,车库的确是已经建好了。
我刚要往里走,突然闻到一股子烟味,还是自己用干烟叶子卷的,我太熟悉这味道了,小时候我爷就老是把我的作业本拿来卷烟叶子。
现在除了一些老人,没人会抽这样的烟。
这里面还有人?
我关掉手电,等适应黑暗,能勉强看清一些东西后,我循着烟味找了过去。
绕过一道梁柱,我看见一个男人正蹲在墙角,手里夹着根烟,狠吸了一口,他把烟踩灭,往地上一躺。
我看了他半天,确定他是个喘气的活人。
在他身下铺着一层纸板,旁边叠着几件脏衣服,衣服旁是筷子和铁饭盒。
他一个大活人咋还住到这里来了?
想了想,我决定上去提醒他一下,就算是再没钱,也不能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这里不能住。”我走过去说。
他蹭的跳起来,第一反应不是跑,竟然是往我脚上看了眼,然后立马把我拽到纸板上,“你个小丫头咋还跑这来了?不知道这不干净?”
我拧眉,他不是误闯进来的流浪汉,是知道这里闹鬼,故意进来的。
“你是啥人?”我挣开他,往后退了两步。
他压低声音,指着我脚下说:“别出这个圈,这里不干净,我就是在这里的睡觉的。”
我低头,才注意到他在纸板周围撒了一圈的木头灰。
“这是土灶烧的柴火灰。”他解释说。
我心中防备起来,用柴火灰驱邪这是农村的土法子,我爷还特地跟我说过其实单纯用柴火灰没啥用,还得加点符灰。
“你也是看脏的?”我问。
他摇头,“我不是,我就是来这里睡觉。”
我不信他这解释:“这附近的人都知道车库里有脏东西,你不要命了,跑这里来睡觉?”
他搓了把脸,苦笑着说:“我这也是没法子,租房子太费钱,我一个月捡瓶子纸板的也就挣一千多,家里还有孩子上学,省点是点。”
我伸手去捻地上的柴火灰,刚碰到手指就火烧火燎的疼,缩回来一瞅,手指肚的皮给烧焦了一块。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柴火灰还真能驱邪,他是个行家。
“你学过看脏?”我打量着他,问。
他扯扯嘴角,神情复杂道:“学过,不过后来遇到点事,一身的本事都废了,现在连点重活都干不了。”
说完,他笑了,“小丫头,咱俩也算半个同行,你说说,你来这干啥?”
我回道:“这有人说这里不干净,给我钱让我过来看看。”
他拍了下我的肩膀,语重心长的劝道:“听我一句劝,有些钱不能挣,你就是挣了也没命花,年纪轻轻的,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好。”
“关于这里,你都知道啥?”我追问,他肯定知道些内情,不然不会这么说。
“嘘!”他冲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把我摁到纸板上,眼睛盯着那条往车库深处延伸的通道。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