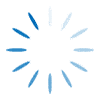龙临一脸坏笑,但是他怎么可能会乖乖听话,索性就直接趴在秦天音身上不起来了,闻着秦天音身上的清香味儿,一脸的沉醉。
秦天音倍感无奈,她还没被人这么占过便宜呢,所以趁龙临放松的时候,腿一发力就顶上了龙临的弱点。
哪知龙临早有防备,一把抓住了她的腿,睁开星子一般明净的眸子,嘴角一勾,就笑了出来。
“就这么点儿本事?”龙临瞧着秦天音,张嘴就是一番嘲讽,说着就一把抓住了她白皙的小脚。她的脚很小,许是在风中吹了一阵儿,所以摸起来又凉又滑,龙临心中升起一种异样的情愫,看着秦天音花容失色的样子,不由得就亲了上去。
她的唇软软的,就像豆腐一般,碰上去滑滑的。
秦天音怔怔得说不出话来,她一脸惊诧得瞪大了眼睛,任由龙临充满暧昧的气息铺天盖地而来,霎时就席卷了她的身心。
“呃……”秦天音一把推开他,忙拉紧了衣衫,不露出来一片肌肤,与此同时她脸红得如同熟透的樱桃一般,看起来娇艳欲滴,让人忍不住想咬上一口。
龙临得了便宜,此时正老老实实得坐在石桌前,脸上挂着满足的笑。
秦天音颇感无奈,龙临这突如其来的暧昧真是让她有些不适应呢。
“这个送给你,就当是我给你的补偿了……”龙临收起镇尺,把自己作的画递给了秦天音。
秦天音脸红不已,此时已经红到了耳根处,可是为了不让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荷尔蒙的气味,秦天音这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接过了龙临递给她的画作。
“送给我?”秦天音端详着龙临的画作,这才发现龙临画的竟然是自己,脸上满是讶然,不得不说龙临的这幅画足够的细腻,而且这工笔画颜色晕染的又极其到位。
秦天音有些怀疑,下意识得瞧了龙临一眼,打探道:“你说这是你画的?我怎么不相信呢……”毕竟龙临给她的印象就是只会舞刀弄枪的糙汉子,又怎么可能画出这么细腻,意境又如此之美的工笔画来。这其中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她还是不敢相信。
画中的女子肤若凝脂,静静地睡在松软的兔毛软毯里,一架的淡粉色蔷薇将她包裹,花瓣随风飘落,正巧落在她用来遮住阳光的薄纱团扇上,她趿着的鞋子摇摇欲坠,颇有一种俏皮之感,只是无不透露着诱惑的意味。
秦天音打量着手中的画作,如获至宝一般,自是爱惜不得,她偷笑出声,盯着画作,暗自自恋起来,我真的有这么好看吗?
一时之间她有些茫然,不知道该说是自己本来就这么美,还是说龙临的画技高超,竟然把她画得宛若仙子一般。
“真好看……”秦天音盯着画作,笑意盈盈。
“你是夸我画得好呢,还是夸你自己呢?”龙临问道。
秦天音抬起墨色的明净的眸子,笑笑说道:“当然是夸我自己的。”
龙临一脸宠溺地点点她的眉心,无奈地摇摇头,不管怎么样,她喜欢就好。
“不过我夸我也等于变相得夸你,夸你画技高超。”秦天音说着就为龙临鼓起掌来,只是还是不敢相信,就疑问道:“不过,这真的是你画的吗?”
龙临没回答她,笑笑不做声,就这么一脸满足地看着秦天音傻笑。
其实当年如果没有进入军营,他应该会画一辈子的,只是世事难料,他竟然会投笔从戎了……
秦天音宝贝的很,卷起来又怕画晕染了,叠起来又怕有折痕,兀自喃喃道:“看来是要找个师傅给裱起来,正好我那房间里缺了这么一副画呢。”
“你喜欢就好……”龙临笑笑,适才说道:“我倒是知道一个裱画的高手,改日我再给你带来。”
秦天音想了想,觉得龙临的主意挺好的,所以就点头同意了。
将画小心翼翼地铺陈开来,秦天音用镇尺重新压上,省得风干墨迹的时候再把宣纸给刮破了。而龙临就坐在一旁,一边吃着茶点,一边看她忙着这些琐碎的事。
秦天音收拾着画作,适才问道:“对了,刺客的事,你都查清楚了?真的跟林长乐无关吗?”
龙临抬起头来,眸色深邃,过了片刻适才点头说道:“确切的说应该是跟他们整个太子府都有关。”龙临冷哼一声,脸上挂着一抹冷笑。
“哦?”秦天音怔了怔,不明所以,“这话怎么说?”
“你可知这刺杀我的刺客有两拨,第一拨功夫很弱,也可以说是不会功夫,只是会点儿拳脚,倒不像是人专门培养的刺客杀手,反而更像是山野村夫打家劫舍的,但是让人费解的是他们又都知道我是谁,若说是山匪打家劫舍,又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这显然不合理。”龙临道。
秦天音点点头,显然认同龙临的说法,她静静地听龙临说着,并没有插嘴。
“第二拨刺客,功夫都不在我之下,而且各个训练有素,出手狠辣,招招致命,很显然就是为了取我的命,倒是像人专门豢养的死士杀手。”龙临眉头微锁,似乎也很是疑惑。“只是我不明白既然想要杀我,又为什么会派了一帮只会拳脚功夫的。”
“这倒是个疑问。”秦天音也想不出来个所以然来。“那现在你知道是谁了吗?”听龙临那么说,他这其中势必经历了重重凶险方才回到京都的,不由得心疼万分。似乎这也是因为自己无意间让别人听去了龙临的行踪,才给他惹下这等祸乱,如果龙临出事,她怕是也不能原谅自己的。
龙临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后来遇到叶华派来的人,我才安全回到京都,在父皇他们大肆寻找我的期间,我和叶华一直在暗中调查这件事。果然让我们发现了猫腻。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两拨刺客都是太子府派出来杀我的,哼……”说着竟冷笑出来,仿佛这其中的危险他根本就不在乎似的。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