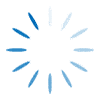荆修竹松开揽住母亲肩膀的手,指尖按在桌沿上,垂眸掩住眼底的心疼,低声说:“他从十三岁开始就给他大哥输血了,一直到现在。”
“十……十三岁!”
荆母是个知识分子,一辈子没做过昧着良心的事情,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一听这种事,怎么能忍,立刻怒道:“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也做得出来?!”
荆修竹怕被外头听见,忙安抚她道:“小声点儿,他不喜欢被人听见这个,小孩儿嘛,脆弱又敏感。”
荆母点头:“我知道,你继续说。”
荆修竹深吸了口气,拍拍她的肩膀,又道:“那家人就当他是买来的商品,讥讽冷眼,羞辱责骂都是家常便饭,你看他这么乖,其实都是保护自己的假象,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肚子里的算计能盖出一个八达岭长城。”
荆母心疼极了,不由得攥紧了荆修竹的手腕,指尖传来的掐疼让荆修竹感觉到,自己说动她了,在心里轻笑了下。
“不对啊。”荆母手指忽然一松,奇怪的问:“那他既然不被他们喜欢,那他哪儿来的钱资助你们的战队?”
荆修竹结合宁见景的遭遇,自己稍稍推断了下,说:“他们家公司之前有过动荡,同时有个新闻爆出来他是血人的事儿,老爷子为了堵住外人的嘴,就说是他是养子,摆出他拥有公司19%股权的文件证明。老爷子去世后,他哥把他送到我手里来管教,两人有了个约定。”
“什么约定?”
“如果一年内,他让俱乐部赔了钱,他就得交出手里所有股权,并清偿俱乐部损失。”
荆修竹话音一落,荆母立刻拍了下桌子,怒道:“这是什么大哥?还给他输了这么长时间的血?这是救了个白眼狼吗!良心都上哪儿去了!太过分了!”
荆修竹立刻添油加醋的说:“他被收养之前还不知道过的是什么日子,收养之后每天提心吊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从他身体里拿走血。小小年纪整天喝酒,把委屈都埋在心底,也不会照顾自己,动不动就搞得一身伤却不让人知道,自己默默舔舐伤口。我要照顾他,他觉得我是外人,不肯。”
荆母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深吸了口气说:“这孩子,真是可怜他了。”
“他这辈子可能都没有感受过母爱,我也是想带他回来吃顿饭,就算不能,让他开心这一天也是好的,以后回忆起来也不是一无所有。”
荆修竹越说,荆母的心越疼,她身为母亲的本能,恨不得立刻就出去将他抱在怀里,说一声孩子苦了你了。
荆母想起刚刚在门口宁见景眼睛微弯乖乖巧巧叫她阿姨,身子骨清瘦下巴瘦的削尖,怎么看怎么惹人疼。
“那他愿意吗?”荆母问。
荆修竹忍笑,已经不需要他来引导,荆母自己就说到重点了。
荆修竹想了想,说:“他会愿意的,你只要装的不知道这些事,只说和他合眼缘,觉得喜欢他,问他能不能认他做干儿子就行了。”
荆修竹说完,荆母有些不信的蹙了下眉,“这么好哄?”
“不是好哄,是他不会拒绝人。”荆修竹顿了顿,谨慎的来回在心里思忖了几遍,又道:“他要是婉拒,你就赶在他之前说,是不是觉得自己只是个穷教师,不配做他干妈,他就不会拒绝你了。”
荆母侧头,看着他忽然尾音上扬的“哎”了一声:“你怎么这么了解他?”
荆修竹眸子一颤,心虚的咳了两声说:“我拿他当弟弟,哪有哥哥不了解弟弟的,好了我出去了,端个菜这么长时间,他要怀疑我了。”
说完,荆修竹端着菜转身出去了。
荆母沉思了一会,抬头看了眼外面漆黑的天色,压下心底的心疼,低低的叹了口气。
可怜的孩子,他得吃多少苦,才能把自己变成个这么坚强的模样啊。
**
饭菜上桌,宁见景洗完手回来规规矩矩地坐在荆修竹的身侧,半起身双手接过荆母递过来的饭,“谢谢阿姨。”
荆母看着他,怎么也忍不住心里的心疼,眼睛红红的摇了下头:“……没事,多吃点啊,别客气,就像在自己家……”
话音一停。
宁见景奇怪的看她,斟酌着问:“怎么了吗阿姨?”
荆母忙道:“没,没事。”
荆父很健谈,刚才在外头和宁见景从国家大事聊到了各国风俗,虽然宁见景对国家大事知之甚少,但偶尔两句也能敷衍过去。
相谈甚欢,连辛故知都有些接不上话了。
吃饭时,辛故知坐在荆母旁边,无声地吃着饭,眼神在两个人身上扫来扫去,今天晚上荆阿姨叫她来吃饭,估计是又想撮合她跟荆修竹呢。
他俩都没那个意思,时间一长就当耳旁风,任你刮,出门分道扬镳该干嘛干嘛。
不过今天晚上,这个年轻的小老板以来,她似乎失宠了呢。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